近日,邯郸13岁初中生被害案引发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再次回到大众视野。如何帮助被害人及其家属?如何回应公众的朴素情感?如何超越个案,从社会治理角度解决乃至预防类似问题发生?《孩子为什么遵守规则:法律社会化与合法性发展》一书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思考与回答。在书中,作者汤姆·R.泰勒、里克·特林克纳指出了“孩子”为什么遵守规则,也指出“孩子”为什么会实施罪错行为。这些讨论中,既有符合人们常识的论证,也有违背人们直觉的论证。
本文摘自《孩子为什么遵守规则:法律社会化与合法性发展》,雷槟硕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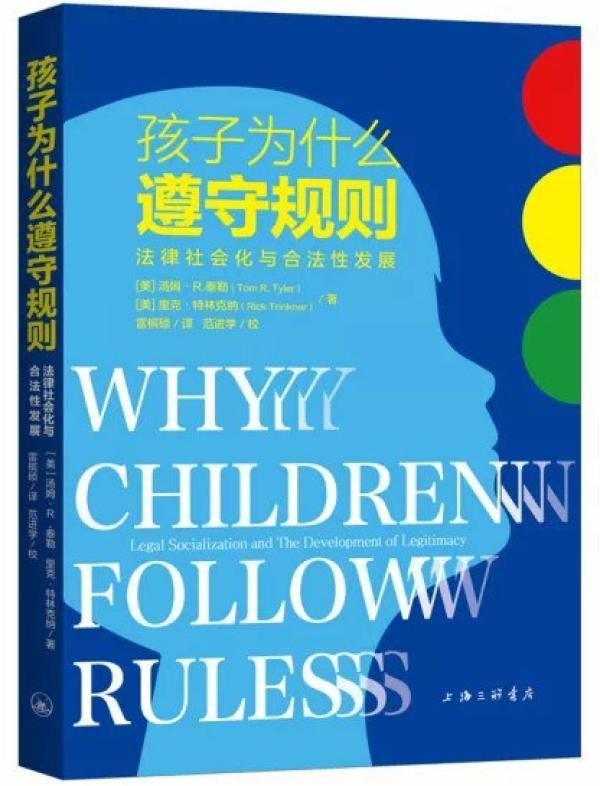
青少年罪错行为的神经学基础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社会情绪系统中的神经活动会出现突然和急剧增长。这些活动的爆发增长促使情感激发与情感反应增强。年轻人的情绪状态开始对行为和认知产生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加敏感。情境线索和其它形式的社会信息在信息处理方式以及世界如何在他们头脑中呈现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当年轻人试图做出决策时,他们更易受到社会影响和同龄人的压力。青春期的许多方面,从默许到形成同龄人压力再到加入帮派,当人们认识到青少年更易受到社会影响时,这些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在奖励机制中,神经化学物质也有爆发性增长,因为人们对有趣的事情更敏感。这种增长同那些受到追求短期目标和奖励指引的想法和行为有关系。
然而,随着青春期的开始,不同于社会情绪系统中活动的爆发性和指数性增长,认知控制系统的发展更像是线性的和渐进的。结果就是,在青少年早期,行为更可能受到情绪激发和社会反应的影响。随着认知控制系统的成熟,人们限制这种反应的能力不断提高。尽管社会和情绪处理依然影响人们的行为与思考,但社会情绪活动更难以凌驾于决策能力之上。
青少年的这种情况就像已经启动的发动机,但把握方向盘的司机却没什么经验。差不多的是,青少年拥有纯粹认知能力,以复杂和抽象的方式来思考他们所处的法律世界;然而,并不是直到最后的神经系统成熟,他们才能合理且有效地使用这些更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发展法律推理能力比掌握思考法律的能力更重要。能够处理和控制其他因素——比如情绪——的这种能力也是必要的。
神经科学研究将自我约束的发展同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神经网络变化联系在一起。在青少年时期,社会情感系统的活动突增,孩子对社会予以奖励的行为变得更加敏感。神经系统的不成熟限制了人们控制冲动的能力,尤其是在神经系统同社会或情绪奖励结果联系在一起时。不出意外的是,参与冒险或寻求的行为,包括反社会行为,在发展时期尤为普遍,导致一些人将青少年时期犯罪行为的激增归咎于发育中的大脑。然而,重要的是理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断增多的违法行为是成长和成熟的一个正常部分而已。青少年通过对法律的努力思考,他们检验着行为的限度,从他们的错误与成功中汲取经验,学习什么是或者什么不是合理行为。这种检验是成长的一个必要部分,也是理解规则价值的一个必要部分,同时也是在令人兴奋和感到诱惑的事实中自我规制策略的一个必要部分。
与此同时,社会情绪系统活动的明显增多,负责执行功能和认知控制发展的大脑部分发展的更缓慢。神经网络根据社区的社会规范负责抑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强大到能够控制社会情绪系统不断增多的活动。与是否实施了一系列反社会行为相关的认知,尤其如此。我们有一段发展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当青少年控制这类行为的能力受到限制,青少年会倾向于实施这类冲动行为。基于此,缺乏冲动控制被认为是违法和犯罪行为的核心要素,就一点都不奇怪了。近来的著作将这种控制缺乏同前额叶皮质发育不足或前额叶皮质受损联系在一起,大脑的这个部分负责认知控制。
这个情况为以下情形提供了一个解释,即为什么这么多犯罪的青少年会以一个守法公民的身份度过他们的成年生活。犯罪—年龄曲线是犯罪科学中最接近“法律”问题的事物。相当有趣的是,当一个人关注按年龄分布的违法频率时会发现,在青少年早期有一个飞跃式增长,这伴随着社会情绪系统中活动的飞跃式增长。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犯罪的频率随之会逐渐地慢慢降低,直到他们进入成年早期,就会稳定下来。这个轨迹同认知控制系统的发展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14-25岁年龄的人是犯罪的主要群体,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在神经学和生物学意义上还处于发育阶段。
直到成年,人们才能像强制模式所设想的那样,才能表现得像一个完全的行为能力人和理性决策者。一个仍在发育的大脑阻碍了青少年思考未来行为结果的能力,尤其是与行为相关的惩罚。与此同时,青少年对情感满足和社会奖励行为高度敏感,威慑被设计出来用以阻止这些。正如斯洛博根和丰达卡罗总结的,“青少年不成熟的最显著特征不是有限的认知能力,而是倾向于冲动行为和屈从于同龄人的压力。”这些要素既是解释违法行为的重要部分,也是因为青少年的特点(冲动、被风险吸引和同龄人驱动行为)使通过使用正式惩戒与惩罚管理青少年行为变得更为复杂。
很大一部分犯罪行为是青少年实施的,而且很多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只在青少年时期实施犯罪行为,这种联系可能性最高的时期就是这段时期。当他们同法律当局打交道时,青少年被带入到一套复杂和正式的青少年司法程序中。
青少年罪错行为的家庭因素考察
心理学家认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孩子们就做道德判断,并按照道德判断行事。这些倾向随后受到环境的影响与塑造。尤其是,家庭和父母是环境的核心要素,其能够促进或损及这些态度与价值观,这对于形成协商性权威的法律社会化是最重要的。当父母在家庭中确立行为规则时、他们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的时,以及他们在规则被违反时维持纪律,父母行使权力和权威的方式特别重要。一般来说,这些关键的互动是孩子们适应日常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的首要途径。考虑到法律社会化的过程,它们作为向孩子传达规则与权威目的的一种手段,为孩子在日后生活中理解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借助强制的管教方式植根于专断控制的趋势。在其中,服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是一种比给孩子灌输其他价值观更重要的价值观。这种方式并不关心权力如何行使以及权威如何运作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相反,与权威的关系被工具化地认为是单向事项。简单来说,成功的父母是能保证孩子服从的父母。父母设定规则,孩子必须服从。如果孩子不服从,他或她必然受到惩罚。好孩子是那些服从的孩子;无论服从是基于自愿的同意或者源于他们对惩戒的恐惧,这都无关紧要。同样,只有服从是重要的,让孩子理解为什么服从更重要。
父母为了让孩子服从,让孩子将服从作为一种价值观,倾向于使用体罚,比如打,来管理孩子的规则违反行为。为促使孩子实施规则服从行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适用了工具主义控制的方法。因为父母并不关注给孩子灌输促使他们自愿服从的价值观,父母必然运用自己的最高权力和地位,对孩子进行管教。然而,讽刺的是,这种管教方式已经被证明无法对价值观发展产生影响。将管教子女的做法同孩子们随后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研究一直表明,体罚在内在控制和减少后来的规则违反行为上收效甚微。
实际上,强制性纪律非但不能促进规则服从行为,更有甚者,会破坏这类行为。强制性纪律不能通过将服从内化为一种价值观,进而促进合作与服从规则。其通常会导致孩子拒绝不值得信任的权威以及导致他们的不服从。比如,专制的管教方式同家庭中不断增多的规则违反行为相关,并会增加孩子采取冒险的行为,比如在家庭以外酗酒和吸食。其他研究直接将体罚同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攻击行为联系在一起。格肖夫与比滕斯基认为,“如果父母的目标是促使孩子道德内化和减少他们的攻击性与反社会行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体罚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是有用的。”
体罚已经被证明会导致孩子采取诸如人际攻击等反社会行为,对促使孩子长期遵守法律基本没用,对于合理价值观的形成并没有作用。相反,体罚可能导致反社会行为,以及导致孩子疏离人群和玩世不恭。比如,在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全国研究中,涉及了3000个孩子和6000对夫妻,施特劳斯将家庭内外的的体罚经历同不断增多的暴力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报告指出,受到最严重体罚的孩子是最有可能受到执法部门逮捕的孩子。后来的研究也将孩提时代的体罚经历同后来成年阶段的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尽管对许多家长而言,这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体罚形式,但施特劳斯认为,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许多暴力行为的征兆。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强调使用强制方式进行管教的两个后果,因为这与法律社会化有关。第一,强制界定了人们对他们与权威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监督侦察和适用强力惩戒违法行为。不是通过内化同法律相关的价值观,这有助于同权威形成积极与健康的关系,而是致力于形成一种排他性工具主义关系,这其中充满了不信任和焦虑,形成纯粹服从是唯一需要的价值观。这种立场促使人们将权威视为无情和冷漠的。
第二,尽管将强制用作控制行为的手段,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制导致了许多不同的规则违反行为。从学校中的校园欺凌到青少年帮派,再到后来的犯罪行为。然而,它不仅使人们对权威概念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分歧,实际上也没实现其致力寻求的结果。基于此,人们会质疑——权威在场的时候——这种方法的成本是否值得立即服从,其带来的好处似乎微不足道,这种方法是否有足够的效用来证成这个模式的正确性吗。
这种盘算的一部分需要是,在适当使用强制时,强制可以影响行为。父母、学校和法律制度亦是如此。如果制度能够妥当利用资源,设定改变的风险和确定的正义,人们能够对惩戒的风险作出回应。对于孩子亦是如此。在他们父母在场和更高的暴力力量强制存在的场合,孩子们倾向于服从他们的父母。而且,立即服从有时也是一个必要的目标。
体罚与许多管教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围绕着纪律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权威的方式可能是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运作的。比如,兰斯福德和同事们研究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母子二元关系,他们发现,当体罚被视为不规范的时候,更有可能导致消极后果。那些体罚不那么普遍的国家,在体罚使用上与孩子的行为问题之间表现出强烈的联系。他们认为,关键是一种方式的使用是否使孩子们认为父母是好的或者是关心人的。另一方面,在所有的文化中,使用体罚会导致孩子更高程度的人际攻击。如果父母用强力控制他们的孩子,他们就是在教他们的孩子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强力控制其他人。
然而,研究普遍指出两个重要的因素,表现为在纪律中使用体罚的征兆和后来违法行为的征兆。第一个是适用纪律的做法前后不一致,在其中体现的是更大范围的管教做法的表征。这个重点是父母在管教孩子时运用权威的方式。父母是否采用公平的方式管教他们的孩子?比如释明决定、允许和保持公开的对话、以透明和连续的方式适用规则。研究表明,惩戒的影响因惩戒被孩子视为公平的程度而不同。再者,适用不公平惩戒程序的消极结果是众所周知和非常普遍的。对于父母,不同的管教方式通常有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父母是否被认为是合法和公平的权威人物。
第二,研究一直指出,一段关系(比如,社会情绪纽带)的存在或不存在在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习得上很重要。无法在情感上与其他人产生联系,以及不能与父母发展出重要的情感联结,会同反社会和违法行为存在联系。同样,母性敌意影响家庭关系纽带,同违法行为存在关系。正如劳布、桑普森和斯威指出,“大量的研究表明,家庭和学校的社会联结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理论上的预测关系。”比如,肯普夫回顾了七十一项研究发现,与父母联系不紧密导致孩子的违法行为增多。
劳布和桑普森认为,那些一直从事犯罪行为的人,“不能与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建立亲密关系或形成任何联系。人们可以认为这些人有扭曲的自主意识,而不关心或在乎其他人”。同样,西蒙斯、约翰逊、康格和埃尔德发现,孩提时代有反社会行为倾向的孩子,如果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发展出稳固的社会纽带后,他们的违法行为就会减少。管教的做法传递出不尊重、轻视或者其他将孩子认为无价值的,以及采取孩子们不能理解的不连续和非透明行为的,会损害孩子们对父母是慈爱以及信任父母的推断,进而使得建立社会纽带变得困难。相反,它们造就了以愤怒、敌意、蔑视和叛逆为特征的关系。
当父母与孩子相处时,父母行使权力的方式确立了孩子理解规则以及他们与权威人物之间关系的框架。这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在孩提时代习得的规则与对权威的最初印象,影响孩子对随后生活中遇到的权威(比如,老师、驻校安全人员、法律执行人员、法官)的倾向。通过这种方式,儿童时期的家庭情况最终影响了青少年和成年之后服从权威以及同权威打交道的倾向。
尤其是,我们已经指出三个影响家庭情况的关键问题:
(1)父母与孩子之间社会纽带的建立,采取表现关爱、关心和有责任心的管教行为。这与传达尊重与慈爱地对待的重要性相关。
(2)父母适用规则和用以规制那些规则违反行为的方式,包括他们试图积极同孩子互动,并采用公平和中立的标准。此处的问题是公平决策。
(3)对孩子试图发挥主动性予以回应,以及父母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和协商自己权威的范围。
青少年罪错行为的学校因素考察
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教育情境下,考察学校环境中孩子的经历如何影响法律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地方,孩子学习同规则和权威打交道,这些事物更遥远和正式化。尽管孩子第一次接触的是老师,老师们与他们的家长一样分享着某些品质(比如,非正式性、长期接触),但学生在一年又一年与任何特定一天的生活中不断接触大量的老师。因此,他们必须学会同更加非个人风格化的权威打交道,这同老师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个过程要学习的内容不局限于与老师进行的私人互动,而且还体现着整个学校的氛围。实际上,学校的整体管教氛围对学生的影响与学生同学校权威人物以及行政管理人员打交道对他们的影响一样重要。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论及学校的文献透漏的信息与关于家庭的研究是类似的。通过严格的纪律和严厉的惩罚管理学校是可能的,但这些策略被发现在推动规则遵从(无论是自愿与否)上缺乏效率。相对应,类似于严厉的父母管教技巧,它们导致的不仅有学校中的规则违反行为,还包括社区之外的规则违反行为。
在另一个方面,可以发现,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对学校环境中的青少年的规则遵从行为有促进作用,而且,支持性态度与价值观与不良同龄人群体以及涉法行为之间存在联系。如果学生认为他们的老师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是合法的——即是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将老师与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看作权威,而且他们相信这些人就是权威——他们便会实施规则遵从行为。学生更不可能参加帮派或者携带武器到学校,更有可能遵守规则与规范,而且它们更不可能实施攻击性的人际行为,比如校园欺凌。
最引人注目的校园环境研究发现,规则公平性的核心问题是规则如何被制定、实施与执行的。研究指出,学校规则的作用首先与它们被视为公平以及决策和待人维度存在很大的关系。研究进一步指出,老师被认为是公平的,这影响了大量学生的成绩,从学术成就到规则遵从都是如此。这些发现与家庭研究文献中的发现是一致的,也认为公平的家庭管教氛围影响孩子对父母颁布的规则与决定的反应。
最后,与父母管教语境下的情形一样,对什么是最有效的学校权威形式存在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有迹象表明人们越来越有兴趣教育孩子关于民主的价值,并维持开放与公平的课堂。这似乎符合年轻人表现出的特点,他们期待更多的程序参与。然而,更成问题的是,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人们支持通过强制性方式管理与规制学生行为。越来越多的学校在处理他们学生的问题时变得越来越不灵活、严厉和刑事司法化。这可以从零容忍政策、规则的严苛、对待校园行为刑事化的意愿中看出端倪,校园内的法律执行人员不断增多使得一些事情便利了很多。尽管学校看起来认识到教授他们学生价值观——法律所内在蕴含——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并不愿意确保将这些价值观内在为学生人格的一部分。
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问这样一个问题是重要的: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谁是合法的权威?老师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是一类发布特定规则的权威。然而,在校期间,孩子加入同龄人群体,在与其他学生打交道时发展出复杂的同龄人网络。在许多情形中,同龄人群体(比如,体育队、学校俱乐部)与权威并行不悖,促进积极的社会发展,并为反社会行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护因素。在其他情形中,学生可能将自己同离经叛道的同龄人群体联系在一起,这些群体代表了权威和规则的其他来源,可能鼓励冒险和违法的行为。其他群体的典型例子就是帮派。
那些越可能不被学校权威接纳的学生或者认为在他们学校中是不受欢迎的学生就越有可能加入到离经叛道的同龄人群体中。帮派的成员身份在另外一套身份体系中提供了一种被尊重和被重视的方式,即使在学校中被边缘化、被停学或者被开除的学生。在这种同龄人群体中的学生不大可能会与权威合作,报告哪些学生携带武器来学校了。与这份研究一样,扬茨认为,错误行为本身可能就是其他同龄人群体具有高度合法性的结果,这种特征的错误行为规范与其他更加传统的学校权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研究进一步指出,对学校缺乏信任影响学生加入一个错误团体的可能性,并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师采取挑衅性行为。
埃姆勒与赖歇尔认为,孩子能拥有两种与权威的关系。他们可以将规则视为“一种约束关系;人们被要求遵守规范,遵从正式明确的禁止规定和指令,服从被授权管理他们的那些人的指示与命令。”另一种关系是一种保障与推动,在这种制度中,给学生提供“权利、他们的人身以及他们的财产的保护,并在他们受到侵犯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救济”。他们认为,当学生经历一个基于约束的正式制度时,他们会需求非制度性方案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对诸如帮派这样的非正式和个人网络产生忠诚。
里奥斯对帮派吸引力的细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青少年加入帮派是寻求保护,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其他权威人物无法提供的。里奥斯认为,存在一个复杂的年轻人控制机制,传统权威将年轻人看作“错误的、有威胁性的、具危险和可能犯罪的”,采用惩罚性社会控制,需要不断地监控、介入和惩戒。最后,里奥斯认为,不断试图约束和控制年轻人会导致他们在他们与外部控制之间的关系中界定权威,因此,当年轻人处于正式权威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变得不能基于内在价值观行动。
除了感到被帮派接纳和尊重外,孩子青睐帮派的一个原因是,在帮派中,权威的运用方式对孩子来说与权威在家庭中的运用方式一样令人熟悉。帮派中的权威具有支配性、工具主义的特点,通过使用暴力来达成它们期冀的目的。尽管关于帮派和欺凌的探讨强调,它们运用权威的方式的不可接受性,但同样重要因此要指出的是,许多家庭社会化的模式使孩子难以理解权威,这涉及到其他观点的讨论与考量。他们可能发现,暴力攻击作为一种管理其他人的方式,与他们早先对权威一般情况的看法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