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历史学家葛兆光录制了访谈节目《十三邀》,“不怕慢,只怕站”是这期节目预告片的标题。尽管已经留下了许多在史学界产生影响的作品,这位已年过七旬的知名学者依然没有停下思考的脚步。他继续推进着已经钻研多年的“从周边看中国”计划,一边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关中国、日本东亚史研究的最新思考,另一边则系统化地整理近十年来授课的讲义,“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力图让更多的学子、学人受益。去年,《葛兆光讲义系列》四卷本已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受到学术圈和大众读者的一致关注与好评。
“内藤湖南是日本人,无论如何,本国的历史记忆、本国的历史问题,始终是最能问题意识的话题”,这是谈及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时葛兆光的一句评价。而对于葛兆光来说,不断地跨出旧有的“边界”,似乎也始终是贯穿在他研究中的一种强烈的“”和冲动。这种“跨界”,是跨出学科与思想的旧有框架,也是跨出国家、地域、族群的边界。
葛兆光, 北京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宗教史。代表作有两卷本《中国思想史》(1998、2001)《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历史中国的内与外》(2017)《亚洲史的研究方法》(2022)等。
1995年,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出版,他着重考察了禅宗各派与、社会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修正了此前禅史研究的许多结论。到了世纪之交的三卷本《中国思想史》时,葛兆光更是鲜明地点出了他全新的方法意识:要打破当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陈规定式,把思想史的眼光从精英身上往下调,更加注重“一般知识和信仰”。自调入复旦大学后,他开始着手推进“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项目,相继推出《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问题的再澄清》三部作品,帮助人们重新反思对中国的旧有认知。
“我们看历史需要多面镜子,一面镜子只能看到一个方向”,这是葛兆光近些年在讲座和媒体上发言反复会提及的一句话。道理很朴素,但有着思想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在葛兆光看来,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依然在推进,但把中国放到全球的视野中,用不同国家的史料反观中国,不断打破中国人过去的许多有关中国的成见和定见,如今依然极为必要。这种尝试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热相呼应,但又有所不同。全球史的范围太广,用葛兆光的话来说,即便是“东亚”,其内部各个国家、地区间的差异都远非我们目前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学家的务实,让葛兆光选择将目光锁定在“东部亚洲海域”,用“国家”与“全球”之间的“区域”,作为自己进一步“从周边看中国”的抓手。2月18日,在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时间的眼睛”上,葛兆光做客论坛“放宽历史的视域从交叠的空间出发看中国”,与罗新、赵世瑜两位学界同行也讨论了“东亚”“亚洲”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的视野,需要“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点击《历史学家是诊断病因,却无法“开刀手术”的医生 |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回顾②》
在葛兆光眼中,15世纪的环东海南海区域,即我们常说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包括明清中国、朝鲜、日本、琉球、暹罗、爪哇等,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世界。许多曾经在单一国家历史中被一笔带过的历史事件,若是放在这个历史世界的背景下,就会被凸显出不一般的全球史意义。
不过,葛兆光仍然保持着视野和方法上的自省,在跨出旧有的边界,将中国人对东亚的理解“去中心化”后,区域史是否比单一国家的历史更值得关注了?当我们过于强调中国“周边”的重要性,是否意味着无形中强化了对“中心”的默认?他觉得,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反思,也是后辈学人应该继续的工作。
本文部分内容刊于2023年3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葛兆光:从亚洲出发,抵达世界》中的B02-B03。此为补充版。
专题其他文章:
葛兆光:在“东风”与“西潮”中追寻中国
冲击与回应的余音:葛兆光的“论中国”
采写|刘亚光
我们经常误解中国和周边国家
之间的差异
新京报:多年前,你就开始主持“从周边看中国”这个项目。从《何为中国》《宅兹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到如今《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中提出的东部亚洲海域史研究,你“从周边看中国”的问题意识有哪些变化?
葛兆光:2000年底我写完了《中国思想史》第二卷。这一卷结束在5年,你知道,5年也就是甲午后的《马关条约》,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从此被彻底卷入现代世界,东亚格局也发生巨变,要讨论此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就不可能脱离开更大的世界或者亚洲背景了。就像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里讲的,过去我们讨论“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乾隆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中国放到“世界之中国”的背景下去审视。本来,我就计划在《中国思想史》第三卷中,把中国思想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继续写,但发现有点写不下去,头绪复杂,史料太多,于是就暂时搁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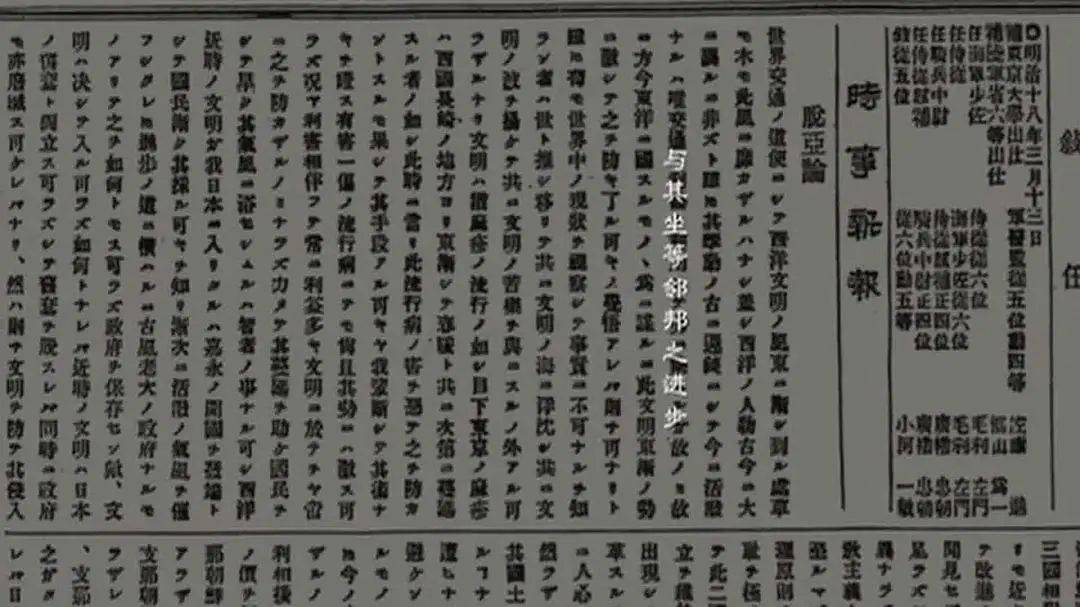
纪录片《甲午》(2015)画面。
到2002年,去台北开会,我的讲题是《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记得当时同场的是林毓生先生、子安宣邦先生,主要是回应日本和韩国学界的亚洲观,显然那时候,我的关注已经从“中国”延伸到“亚洲”。同一年,我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宅兹中国》一书的副标题“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这篇文章还引出了林同济先生的回应,我觉得,晚清以后来讨论中国,如果不弄清“周边”,不观察“世界”,我们根本不可能界定清楚何为“中国”,更不要说建立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为什么?因为传统帝国时代,疆域可能无边无涯,有边疆而无边界。但近代以来,都认同主权国家有明确的边界、主权、国民,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借助“他者”来界定“我者”,这时候“周边”意义就越发凸显了。
《想象异域》,葛兆光 著,中华书局,2014年1月。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看各种朝鲜燕行录,后来就写了《想象异域》一书,来讨论东亚各国的认同问题。现在想,之所以我会把目光投向周边,大概原因是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需要多几面镜子。过去我们讨论中国,历史对比中依赖西方主要是西欧比较多,对自己周边列国的关注反而不够。特别是过去中国有“天朝上国”的观念,在文化上比较傲慢自负,再加上觉得本国史料“汗牛充栋”,很容易觉得周边这些国家的史料不重要,也容易把周边国家看成和自己同质的文化圈,似乎韩国、日本、越南都是汉字文化圈,是我们的学生,导致我们经常误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共性,却忽略它们之间的差异。所以我经常讲,中国和日本、朝鲜、越南的差异,并不比中国和法国、德国、美国的差异小。我最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概会在3月发表,讨论的就是传统中日之间在文化方面巨大的差异。
2006年,我开始推动“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方向,到了近年,有了一些更为现实的关切。你知道,历史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培养爱国主义,塑造国民的意识。二是培养世界公民意识,让我们的心胸向世界开放。传统中国在狭隘封闭的状态里停留较久,我想更需要通过重新认识“世界”“周边”和“中国”,来警醒自己,学会平等与世界交往,尊重周边的民族与国家,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保持距离。
新京报:我们知道,古代朝鲜的史料大多用汉文书写,和古代中国也关系密切。但朝鲜史料的发掘,以及相关研究似乎受到的重视还不太够。从你近些年对东部亚洲海域的研究经验看,朝鲜对于“从周边看中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葛兆光:近年来,你说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当年,胡适在世界历史学大会上强调有关中国的日韩文献的意义,吴晗选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时候,甚至到我们提倡“从周边看中国”研究方向的时候,学界还没有那么重视朝鲜史料,但近十几年来,朝鲜史料已经非常受关注,甚至是热点了。很多学者都在用朝鲜的汉文文献进行研究,不仅仅过去熟知的《漂海录》《热河日记》,也不仅仅是《李朝实录》和各种朝鲜文集,也包括通信使文献、朝鲜王朝的各种档案汇编,像《同文汇考》《备边司誊录》之类,都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了。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 辑,中华书局,2022年10月。
这个变化很大,朝鲜史料包括日本史料的意义,容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说,第一是补充了中国本身史料的不足,因为历史上有些史料在中国被遮蔽或者被遗失,它们补上了这些缺失的环节或场景;第二是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观看中国历史的新角度与新立场,使得我们看中国,不再是俗话说的“自己看自己,越看越欢喜”;第三是把中国史放在东北亚甚至更大的历史中,从而中国史变成了或融入了世界史或者亚洲史。
新京报:你曾多次前往日本访学,和日本学者也建立了很好的学术往来。日本在思想史方面有着很深厚的积淀,从和辻哲郎、村冈典嗣到丸山真男等都留下了影响深远的作品。就你的观察来看,近些年日本的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向和议题?
葛兆光:近些年来,我去日本访学时,有意识地稍稍改变过去的习惯。过去,去京都大学也好,东京大学也好,多数是和自己熟悉的日本中国学研究者交流,因为话题相近,思路相近,谈话内容也很容易。但近年来,我有意识地和研究日本史的日本学者多交谈,像研究日本思想的渡边浩,研究日本宗教的末木文美士,研究日本历史的村井章介,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研究本国(中国)史的学者和日本研究本国(日本)史的学者,在针对“本国”的问题、关怀和思路上,有更多相近之处,所以,也同样容易沟通和理解,也有更多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
说到日本思想史研究。你看过末木文美士的《日本思想史》吧?他在全书之末说到,日本思想史研究似乎在衰落,因为只剩下仙台东北大学还保留了一个讲座。
《日本思想史》,[日]末木文美士 著,王颂、杜敬婷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这当然是一方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日本思想史领域,由于有你提到的和辻哲郎、村冈典嗣到丸山真男,特别是思想史领域的丸山真男,影响极为深远,他们提出的种种话题,仍然在发酵和深化,现在如果你去看日本书店里出版的新书,日本的“国体”问题和“”问题、日本的“忠诚与叛逆”即伦理问题、“受容与变容”即日本对外来思想的接受与改造问题,还是很多著作不断出来。如果你再注意到黑田俊雄的“显密体制”论,安丸良夫和色川大吉的“民众思想史”论,不仅涉及宗教信仰,也下及社会思潮,你就会知道,日本思想史的现状,并不像西方思想史领域那样,仿佛“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这是我的朋友黄进兴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状况的比喻),而是“化身万千”,仍然主导着很多思想、学术和历史议题。
传统中国的历史记忆
需要“创造性的转化”
新京报:末木文美士的《日本思想史》去年年底引进了中译本,他在书中将日本思想史的基本图式归纳为“王权”与“神佛”。对于日本来说,作为思想的“王权”与作为宗教思想的“神佛”一明一暗,始终在互动和拉扯中,这个过程塑造了日本的思想。不过你也提到,这种“王权”与“神佛”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在中国并不明显。日本的王权神圣性源于血统,存在一个“重层结构”,不似中国的“绝对专制”。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这种“王权”和“神佛”之间的张力?中日两国的这种差异,对他们看待自身以及“周边”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葛兆光:我在最近撰写的一篇长文《什么是传统中日文化的结构性差异》中,已经仔细谈到这个问题。这里只能简单说,我觉得,因为自秦汉以来,古代中国把、信仰和知识垄断在“予一人”手里,大权在一人一家手里,他笼罩一切领域,管天管地管空气,所以,传统中国宗教从来不可能超越皇权,宗教信仰从来都只能匍匐在皇权之下,即所谓“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你宗,如果想常转,那必须先祈求皇图永固。这不像日本有黑田俊雄所谓“权门体制”,公家()、武家(将军)、寺家(宗教)三足鼎立,形成某种平衡,所以在传统中国历史中,宗教能够掀起的波澜并不大,这是中日之间文化的大不同之一。因此,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你看到日本宗教介入很深,比如明治维新中有“神佛分离”的举措,借助本土神道教,以神代史重塑权威,形成集权的帝国与王权,来推动近代化进程,而中国宗教,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好像非常边缘,除了“庙产兴学”、“建立孔教”等不多的事件之外,中国现代转型中,宗教的意义并不大。
新京报:在《宅兹中国》里,你曾经提到一个判断,中国知识人始终有着很浓厚的“天下主义”,这种思想资源有时能转化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但有时又会蜕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从具体的历史事件来看,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的状态?
葛兆光:如果传统的“天下观念”剥离了朝贡体系的历史记忆和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并接受现代国际秩序规范,自觉自愿地融入世界,那么也许这种“胸怀天下”的传统,可以帮助我们知识人接受“世界主义”,但是,如果简单把传统的“天下主义”拿来,仍然暗含天朝中心意识,作为另起炉灶,通过恢复帝国记忆以对抗现行世界秩序的思想工具,那么就会蜕变为狭隘的、伪装成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传统中国的历史记忆很深,有关世界的观念往那边靠,全看你是否有林毓生先生说的“创造性的转化”。
《宅兹中国》,葛兆光 著,中华书局,2011年2月。
历史研究需要“去中心化”
也需要“再中心化”
新京报:在这些有关“周边”的研究中,你一方面强调通过学习周边国家的史料、研究,了解他们如何审视自己与中国,一方面也强调我们要站在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上,用一种更大的“周边”视角来重新发现“周边”中的中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从周边看中国”?
葛兆光: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然是史料。1938年胡适在第一次世界历史学大会上就说过,除了我们常说的“发现”以外,还有第发现,就是日本、韩国所保存的有关中国的史料,它们非常丰富,可以让我们借用“异域之眼”来反观自己。其实,不光是日本、韩国,其实,周边还可以再大一点,比如蒙古、印度、东南亚、中亚的人怎么看中国?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所以,“从周边看中国”首先是对多元化史料的重视。
第二,“从周边看中国”能让我们以一种更宏阔的视角来反观历史。我在一次演讲中讲到一个案例,663年发生在朝鲜半岛的“白江村之战”,这个事件如果仅从大唐的角度看,它并没有那么重要,《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并不多,但从日本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决定日本后来国家历史命运的一战,在朝鲜半岛,这一战前后,新罗大唐化并且统一半岛,这也决定了后来朝鲜半岛文化发展方向。但是如果你只看中国史,其实白村江之战对大唐来说,它只是安定东部的小事,因为大唐帝国最关心的,最感威胁的,当然是西边,突厥、吐谷浑、吐蕃等。所以,仅仅站在一国历史位置,我们看不到它在更宏大的历史中的意义。
2月18日,葛兆光现场连线2022新京报阅读盛典第二场活动“放宽历史的视域从交叠的空间出发看中国”,谈历史学研究是否需要“再中心化”。
第三,“从周边看中国”既是方法也是立场。我在参加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时,提到了历史研究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问题。
关注“周边”,一个重要方意义,就是把过去一国历史中很多中心化的、固执的历史叙述先“打散”。我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里提到十三世纪的“蒙古袭来”,如果说,汉唐以来中国一直相信自己是天朝上国,华夏文化笼罩四方,那么,“蒙古袭来”事件之后,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认知就有了变化。到了明清易代,日本、朝鲜甚至认为中国已经“华夷变态”。如果我们借用他们的角度和立场反观中国,很多固执的自我想象,就瓦解掉了。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葛兆光 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
当然,“从周边看中国”有时候也让人误解,认为“周边”这个词,依然是在把中国当作“中心”,韩国的白永瑞教授就提到,应该用“双重周边”,韩国是中国“周边”,中国也是韩国“周边”。其实我完全赞同这种说法,我甚至说,不是“双重”,应该是“多重”,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都可以从“周边”来看自己。当然,“从周边看”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没有背景和焦点,因为历史学者观看历史的时候,都一定会站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和角度,所以,“再中心化”“再脉络化”依然是必须的,但经过了“去中心化”,历史观看的图景已经被重构了,这时候再形成的“中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永恒、僵化和固执的,只是在某种背景下被映衬出来的聚焦点。
《思想东亚》,[韩]白永瑞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
新京报:如果我们注定需要“中心”,那么对全球史研究来说,有更“合适”的“中心”吗?还是说其实它们都只不过是不同的角度,并无高下之别?
葛兆光:咱们说“中心”,就等于说“聚焦”。霍布斯鲍姆的帝国四部曲其实就给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提炼了一些“焦点”,用精炼的概念来抓住它,当然,这个焦点可能是一种“时代精神”或“时代特征”。霍布斯鲍姆提炼的这几个概念,“帝国”“资本”“革命”“极端”很有笼罩力,但凡是概念,就不可避免地有聚焦也有疏漏,就像照相,焦点清楚,但也有被模糊的地方。
霍布斯鲍姆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四部书被称为“年代四部曲”,而前三部则被称为“19世纪三部曲”。 贾士蘅、张晓华、郑明萱、王章辉 等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
又比如,17-18世纪帝国争霸,羽田正对于“帝国”曾经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他说,有的帝国中心和殖民地的关系就像“荷包蛋”,帝国像蛋黄在中心,殖民地像蛋白在外边,但还有一种帝国是“炒鸡蛋”,没有中心,蛋黄蛋白混成一团。当我们讨论17-18世纪的帝国争霸时,怎样想象帝国,这个比喻是非常有解释力的,当时新老帝国争霸是主旋律,大航海时代之后陆续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就是典型的“荷包蛋”,依赖海洋控制远方的殖民地,而中国等老帝国就像“炒鸡蛋”,是在陆地上从中心向四周弥散,控制广大的族群和边地。这是不是可以作为理解当时帝国争霸史的一个入口?当然,概念并不是历史,历史总是比概念丰富,一个焦点,一个概念,在这儿适用,放在别的地方不见得好用。
我一直强调,历史学家不能傲慢地认为自己像上帝有“全知”视角,即便做全球史,我们也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历史学家其实最痛恨“无秩序”,没有一定的“秩序”,我们难以从历史中看出任何东西。因此,“中心”或者“聚焦”就不可避免,我说的“去中心化”“去脉络化”之后必然要“再中心化”“再脉络化”,就是这个道理。
新京报:很早之前你就曾提出过“新思想史”的说法,主张把社会史、知识史、法律史等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领域打通,同时既要重视精英的正典思想,也要关注边缘的、民间的思潮,力求获得对思想发生语境的一个整体性理解。在“新思想史”这种视野之下,是否“思想”无所不包,任何对象都可以成为思想史的对象?
葛兆光:和刚刚我们聊到的“去中心化”、“再中心化”问题类似。我觉得,我对思想史的思考中,最重要的是先把画地为牢的界限打破,先“破”才可能“立”。从《中国思想史》到后来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我特别强调的是,不仅要关注思想的提出,更重要的是关注思想的落实。天才的灵光一现,固然伟大,但可能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影响,就像王夫之的思想著作虽然著于明清,但真正发生影响是在清朝后期。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葛兆光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
关于思想的落实,我也常讲,主要是三个维度,一是制度化,即思想如何转化成制度,就像儒家之所以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最深的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儒法合流,文吏合一,在汉代之后,它形成了规范人们公私生活的法律制度,在社会层面对日常生活伦理形成了控制,这就是法律史研究中常说的强调“礼法合一”。二是思想的常识化,如何通过教育、阅读,让民众接受来自精英的思想,这很重要,这就要考虑书院、科举、学校等。三是思想的风俗化。一个时代发挥最大作用的思想,经常不是人们被迫地、理性地去接受的,而是融化在风俗中,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感染人的。去年,岸本美绪的《风俗与历史观》大家都很关注,这本书想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从这三方面入手研究思想史,确实,好像思想史原来的边界被打破了。可是如果你想有新变,至少要先把僵化的边界尽可能松动,先往这个方向走,至于重新构建新的中心和脉络,我想这需要后来的学者继续思考和努力。
新京报:你治思想史多年,也和同为思想史大家的余英时先生有过很多私交。在美国华人学界,余英时、张灏、林毓生被称为“思想史研究三杰”,这两年他们也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身上有很多类似的气质,比如对传统和现代的兼容并包、对乌托邦的警惕、广博贯通的知识背景等。你会怎么理解这一代学人为思想史研究留下的遗产?
葛兆光:余英时、林毓生、张灏三位先生,我都有不少交往,留下很多记忆。当然因为我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全球学人”四年,那几年常去普林斯顿,所以,和余英时先生往来就最多,他去世后,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题目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传薪者》,我用“传薪”这个词表达我的想法,也就是说就像薪尽火传,我们必须在他们的延长线上,继续往前走。
毫无疑问,他们三位都是杰出的学者。我完全同意你的概括,他们确实都有“对传统和现代的兼容并包、对乌托邦的警惕、广博贯通的知识背景”这些特点,让人感受很深的是他们的人格和精神,他们对学问的专注,让我们感受到“学术作为志业”的意义,他们对中国深切的关怀,也让我们理解书斋学术与现实问题之间的联系,甚至他们对于生活、生命、他人的态度,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真正学者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在这一两年中先后往生,让我们觉得很悲凉。
提出“东部亚洲海域史”
的意义
新京报: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中,你写道,“当我们注意到、、贸易、宗教和语言的交错影响,就应当注意到超越国别、放大区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史有点儿窄了,而‘东部亚洲海域史’则很有意义了”。是否可以具体展开谈谈“东亚史”和“东部亚洲海域史”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葛兆光: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东部亚洲海域”这个词很别扭,为什么搞六个字那么长?直接说“东亚”不就行了吗?
其实,用这个概念还是有两方面特别考虑的。一方面,过往的所谓“东亚”,往往只有东北亚,即便再扩大一点视野,经常也只有“汉字文化圈”。我的考虑是,用东部亚洲海域这个说法,把东北亚、东南亚、环东海、环南海连接起来。15世纪以后的中国其实有一个转向,当时鞑靼、瓦剌、吐鲁番,其实把明朝西边的通道大体阻隔了,明代中国的重心,其实在逐步向东边海域转移,当时中国的朝贡国都是来自东边南边。其实清代也一样,而十六世纪后欧洲殖民者也是从海洋来。这个转变的意义经常为人忽视,虽然东边的海洋,从“背海立国”的宋朝起就对中国影响很大,到了明朝永乐以后更是如此,但历史给予的重视并不多。

明代《山海舆地全图》。
这也涉及日本学者的“东亚”概念,日本学界深受西嶋定生影响,西嶋定生是把“东亚”和中国连在一起的,汉字、佛教、儒家、律令制国家,构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所以当他一提到东亚,中国就是中心,中国文化就是笼罩整个东亚的。日本学者近年来反思这个说法,认为它过于以中国为中心。我们承认,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尽管中古时期,可能情况确实如此,东北亚以及越南深受中国影响,但是,15世纪后,必须把过去所谓“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比如同样与中国关系很密切的东南亚算进来,那里还有深受印度影响的部分呢,不止是安南,你看暹罗、真腊、爪哇、苏门答腊、勃泥、吕宋,你就得超越“汉字文化圈”,就是原来所谓“东亚”。如果你再考虑后来进入亚洲东部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你得把环东海、环南海连成一块,才能说明那个时代的历史状况。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试图回应现在流行的“欧亚”或者“东部欧亚”理论。2020年疫情期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感到许多日本学者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欧亚”这个概念原本聚焦在北方,也就是从朝鲜、东北、蒙古、新疆、中亚、西亚一直到欧洲,寒带和温带交汇的那一线。这个概念是以内亚为中心,把北方的各个族群连起来,这有它的道理。因为过去东亚史叙述太突出汉族中国,现在有了这个视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的历史都能重新受到重视,连成一片。不过,我当时和他们讨论时就提出,这种说法强调了东西向的历史联系,但忽略了南北向的重要性,适合了中古时代,而未必适合近世,15世纪以后,从库页岛到爪哇,包括中国东部南部地区在内的环东海南海海域,其实是联系很紧密的一块区域,无论是上的朝贡圈还是贸易上的海上交通,包括后来的欧洲殖民者、传教士、商人,都活跃在这条南北向的海域中,我们应当怎么说明这个南北轴的重要性?所以,我想用“东部亚洲海域”这个概念,把这片区域打通,将它作为一个类似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世界”去考察。
其实到今天,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在15世纪以后其实是一个“背向陆地,面向海洋”的帝国——即便是中国自己都有点儿忽略,所以,晚清才有“塞防”和“海防”之争。其实,李鸿章他们看得很对,东面的海洋越来越重要。虽然在那之前的传统中国,绝大部分威胁都是从西北来。这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后患。中国在近代落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失去了海洋”。
2月18日,葛兆光现场连线2022新京报阅读盛典第二场活动“放宽历史的视域从交叠的空间出发看中国”。点击图片可打开现场回顾文章。
专业的历史学者
必须“保卫历史”
新京报:当今学术界中,对何谓研究之“创新”似乎也缺乏一个较为有共识的标准。在你看来,一个能带来全新“图景”的概念工具是怎样的?
葛兆光:还是以思想史为例吧。当时我写《中国思想史》引发了很多争论,主要是因为我说要写“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这在当时可能是一个新提法,也是后来20多年里我的思想史被讨论最多的概念。我当时用这个概念,首先当然是为破除过去认为思想史仅仅属于精英、把思想史写成了哲学史的偏见。其次是想把思想史的重心从思想的提出,多多少少转向思想的落实,再次是我希望把思想史和知识史打通起来。思想的合理性往往是靠知识来支撑的,如果抽掉了知识,思想就变得玄而又玄,失去了语境。人们对天文地理、万物运行的观察,对五行风水的论述,这些才是支持思想成立,并且促成思想落实的地方。
《中国思想史(三卷本)》,葛兆光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学术研究里面,不管一个概念本身是否正确,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它引起的争鸣或跟进,和它导致固有观念的松动,才是有价值的。比如,费正清的“皇权不下县”,后来的研究者质疑这个概念,用各种材料证明中国皇权控制很强,古代基层社会治理很细,但如果没有提出这个说法,皇权问题、基层社会问题、乡绅问题,会成为研究者的聚焦点吗?还有大家熟悉的“资本主义萌芽”“李约瑟难题”“关中本位”说,这些概念不管对不对,都开启了重要的研究领域,它本身可能有很多问题,但却引领或后学者不得不跟着讨论。这就是概念、理论的“探照灯”效应。
新京报:你会怎么看知识分子和现实的距离这个问题?
葛兆光:我们不应该否认,历史研究本身有多种功能。比如爱国主义教育,世界主义启蒙,也有娱乐大众。我其实都不反对,但作为专业学者,还是应该尽自己的职责去发掘或逼近历史真相。这个根本立场,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坚守,不能用一种后现代立场,认为真相是不存在的。
《声回响转》,葛兆光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壹卷YeBook,2023年2月。
现在的问题恐怕是,商业诱惑太强,媒体力量太大,历史学者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因此,历史学者面临选择,究竟是降低门槛将就和迎合听众的趣味,还是继续用专业知识尽可能引领和提升读者对历史的理解?
这个问题,其实十几年前就在议论,记得我和李泽厚都谈过关于央视百家讲坛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这个形式可以尝试,但需要警惕,因为它容易让专业学者被大众牵着跑,让学院学者商业化娱乐化。所以,我一直不太敢上电视、录视频或音频。但是,现在相对于广播电视时代,网络媒体影响更强大,有时候不得不介入这个领域,那怎么办?很简单,我只能用比专业研究更多精力去把它做好。你可能知道,近年来我在“看理想”组织一个“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的音频节目,我花了非常多的劲,有三年的时间,我有至少一半的精力都放在这里,每一篇讲稿我都会亲自改,有些甚至会重写。如果历史学家要走向公众,我觉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它以有足够的思想和学术含量的模样走出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北京图书市集·春季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