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家理想谷”谷主,这大概是麦家最舒适的一个身份。“每次我看到这里坐满读书的人,我就觉得很安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天下太平”。
访谈初始,麦家近乎雀跃地为我们介绍这座栖于西溪湿地偏安一角的小型图书馆,这里的旧书满是被翻阅过的痕迹,他目光平和地扫过书架,“每一本破烂的书,其实都在缝补读者的内心。”
此刻的麦家与之后访谈中逐渐清晰起来的那个在童年因为出身被老师言语霸凌的小男孩,或者在父亲灵堂前赶书稿到崩溃大哭的畅销书作家的形象,相去甚远。
父亲灵堂前这次大哭,宿命一般等在麦家因谍战文学名声大噪的路上,“一边给父亲送终,另外一边给‘稿子’送终”,这篇稿子,即麦家最后一部谍战《刀尖》。拒斥“谍战之父”这一头衔的麦家,就此搁笔,之后三年他只字未写,结束了谍战文学的创作。
身价最高的时候走出创作舒适区,带着自己在商业上并不看好的《人生海海》回来后,麦家作品再次大卖:“写作还是我的一个宿命,逃不掉的,即使想逃,最后还是要回来。”
以下为此次访谈的文字实录。

△麦家 x 凤凰网读书
Part 1 时代
“躺平啥风景都看不到了”
凤凰网读书:您现在拥有这么大的名声,您能屏蔽掉那些声音吗?不管好的坏的。
麦家:首先,没有名气,一个作家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前还谈何名气?如果说名气,也是一些读书圈内的人可能会知道我,今天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文学为中心的时代,当然文学也不需要进入中心。
我跟你说一件让我很悲哀的事情,我在8月16日完成了一部新的作品,有一位很著名的主编看了以后说“我真佩服你”,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今天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作,现在除了我们这种人没有人看,他说我告诉你,现在抖音上所谓的第一男性“抖王”,是个“秀才”。我当然没看过。
凤凰网读书:我也没看过,我听过别人的描述,但还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注他。
麦家:他跟我说,你知道有多少人看他吗?一个晚上就过亿,那我们几十年下来,积累了几百万读者,还会觉得沾沾自喜吗?
我不满足于这种过亿,当然如果有一天我的作品被过亿的人阅读,我也会很开心。首先我没有这个指望,我知道这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抖王”,也有“抖后”,但这个时代其实也需要我们。
不能说我们是精英,但是需要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庄重的、比较有探索的、比较有责任感的作品,就像体育,大家都在健身、都在养生,但依然还是需要一些运动员去不断摸高、跑快,他们探索的是人类身体的极限,我们作家,包括很多艺术家,探索的可能是一种智力的、情感的、思想的极限……
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存在,这也是我一直觉得甘于过这样的生活,也愿意为它一直去努力的原因。我觉得我读书、我写作是有意义的,虽然这个意义没有“抖王”“抖后”那么普及,但这并不是数量决定的,放到一种时间维度里,数量可能是很次要的。

△ 麦家 / 摄影 黎晓亮
凤凰网读书:您说您的性子比较慢,但这个时代恰好需要更快的东西,所以是对不上的。
麦家:就是一直对不上,真的。我一直落后于这个时代,我至今都不用微信,有时候甚至有意让自己落后于这个时代。
有一点点不合拍会变成一种落伍,但当你有意识去落伍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有时候回归也是一种创新,当大家抛弃故事、反对故事的时候,我来重新强调故事,这本身是退步,但这种退步有时候也是一种创新,因为它也是一种冒险。我觉得我从《解密》《暗算》等所谓的特情文学转到《人生海海》,其实也是一种“退步”。
凤凰网读书:怎么说呢?
麦家:我又退到了乡村体裁去了,乡村显然不是文学的畅销领域,应该写写职场,写写当代人的内心纠结,这些可能是现在人们比较关心的。我写一个特殊年代的农村故事,可能当代人不一定关心,这也是一种退步,至少不是追时髦,我一直在反时髦,反而一定程度其实也是一种时髦。
我老婆、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经常会说我,麦家你太实了,如果你真正要把自己做大,你身上必须要有点妖气。我觉得这当然有道理。
凤凰网读书:我大概了解您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作家需要妖吗?
麦家:现在是争奇斗艳的时代,但我确实不擅长,甚至是排斥,我爱人一直鼓励我做一点视频,她说应该谈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包括应该去做一些节目,甚至她也把我送上《王牌对王牌》。

△2022年春,麦家做客《王牌对王牌》
凤凰网读书:您会抵触吗?比如说做视频号或以视频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麦家:关键是不擅长,如果擅长我也会去做。我真的不擅长,害怕镜头,哪怕是我们自己员工给我拍我都会紧张。
凤凰网读书:比如说如果想让您聊一些更贴近年轻人的话题,您觉得这些话题有得聊吗?
麦家:我会去聊的有些东西可能会冒犯年轻人。
凤凰网读书:比如说呢?
麦家:比如说我就不能接受躺平。
凤凰网读书:当然您不是一个躺平的人。
麦家:我也不能接受所谓的“享受缺德人生”。
凤凰网读书:“享受缺德人生”这个我还真没听过,但您说躺平的时候,我就心想,麦老师是一个全天下人躺平他都不会躺平的人。
麦家:躺平多没意思,躺平啥风景都看不到了。
Part2 刀尖
“我们的二战文学,一直都有所欠缺”
凤凰网读书:大家都知道您是“谍战之父”,《刀尖》其实就是您宣布告别谍战题材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们要不就聊聊《刀尖》,因为电影也快上映了(注:《刀尖》已于11月24日上映)您看过了吗?
麦家:没有,我觉得保持一定神秘感也挺好的。
当然我们都希望它能被观众喜欢,我觉得一部电影让我喜欢其实比较难,任何改编要让原著(作者)满意的可能性是最小的,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满意,所有观众都满意,还有一个人不满意,就是原著(作者)。

△电影《刀尖》海报
我发现一个例子,到拍出来电影几乎没有改变的,就是《肖申克的救赎》,从叙事、情节几乎一成不变。《教父》《美国往事》,包括《断背山》,这些我都看过原文,都有比较大的改编,但《肖申克的救赎》和、电影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这样的作品其实少之又少。
凤凰网读书:我没想到您也没看过,所以现在对于电影来说,您跟我在同一起跑线。《刀尖》原著分成两本书,一本“阳面”,一本“阴面”,经过电影版大刀阔斧改编后,我期待怎么处理这个视角问题。
麦家:我也蛮期待的,因为确实双重视角对电影来说,很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文学文本里有两个视角,读者会在两个时间段阅读“阳面”与“阴面”,当电影揉到一起的时候,弄不好会视角混乱,给观众制造欣赏难度。电影是要把难度解决掉,这不是说要迎合观众,而是电影艺术必须要完成一个任务,所谓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当然也有一些是探索性的电影,比如伯格曼的《野草莓》或法国新浪潮的一些电影,但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样的电影简直是毒药,因为今天的观众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被心灵鸡汤滋润的一群读者、一群观众,他们不爱钻牛角尖,他们喜欢被人喂着。
这话他们可能不爱听,但在这个时代面前,任何和时代背道而驰的事情,最后都要败下阵来。所以我现在一直奉劝那些导演,一定要懂得在走向读者、观众之间有个暗道,这个暗道它肯定是既是高雅的,又是通俗的。
凤凰网读书:我读《刀尖》的时候留意到,里面所有特工的名字都是南京的地名,您之前在南京工作过吗?
麦家:我以前在军中呆过17年,其中有4年是在南京,所以南京比较著名的景点我都知道。
这部其实发生在汪伪时期,以当时的地名来给这些特工代号,我觉得既是和城市的合拍,也是一种讨巧,著名的景点大家一看就记住了,莫愁湖、玄武门、鸡鸣寺等等……我希望读者更多在剧情、在人物的悲欢离合,而不要在地名、人名、代号上去耗费心力。
凤凰网读书:您在写这种的时候,大概要做哪些资料上的准备?
麦家: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工作,首先这些历史谁都知道,汪伪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残酷的特务机构“76号院”,南京肯定也会有它的机构。大的历史背景不能有错,就可以进入虚构了。
我觉得虚构并不是虚假,虚构其实是要追求更高级的真实,这个对我来说驾轻就熟,也是我觉得一个家最基本的基本功,就是在一个大历史背景下构建一个细部的人物关系,通过这些人物关系构建一个好看的、惊险的、回味无穷的故事。
如果能够赋予这个故事一点点哲学意味,它就更高级了;如果哲学意味赋不进去,赋予一点我们的民族性,或者放进去一种我们的历史积淀,我觉得也可以。像《刀尖》就很难放点哲学意味进去,更多是把一种家国情怀放进去,把当时那种历史惨淡的一面体现出来。
我内心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很少对人说起,比如有大量的影视作品讲述二战期间犹太人被德国人剿杀,而我们中国抗日14年、牺牲了3000多万人,但与欧洲相比,我们的二战文学或文艺作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一直都有所欠缺。我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是不希望后人忘掉这段历史。
当然,耿耿于怀是不是一种狭隘?但是彻底忘掉是不是一种无知愚昧?我觉得这都值得探讨。反正我觉得那段历史在等着中国作家和导演创造更多作品出来,我内心也一直有着这样的期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出来,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有类似《辛德勒名单》这样的作品反映出那段历史,同时也表现出中国人在那段历史中的付出和牺牲。
Part 3 宿命
“我不喜欢‘谍战之父’这个头衔”
凤凰网读书:我在看您的履历时,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您做的好多事情都是以8年、10年、11年这样比较长的时间刻度来标记的,比如说您的第一部长篇《解密》,是写了11年?
麦家:对,推翻了17次。
凤凰网读书:我们人生中能有几个11年,对吧?
麦家:是的,包括我的新作《人生海海》,也是8年以后才写出来,我属于那种不是很聪明、不是很灵光的人,我觉得我唯一自我欣赏的一个优点,就是我能够耐得住的寂寞,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让人寂寞的人,注定了我只能把时间交给自己,但也不能每天在那发呆,总要做一点事吧,阅读、写作确实是最符合我本性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很感谢这个世界有读书、写作这两件事,如果没有这两件事,我觉得我这一生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发。
凤凰网读书:在您的印象中,就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或某一个时刻是比较兴奋的?或者跟您刚刚说的耐得住寂寞不太一样的状态,一直都没有过吗?
麦家:我太太知道,我唯一放松就是在家里、在孩子面前,我会有一种儿童态,会欢欢跳跳的,在公众面前我是比较笨拙、比较怯场的,经常手足无措,就是不知道怎样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安放自己,只能把自己交给自己。
凤凰网读书:没有小孩之前怎么放松呢?在这么漫长的青春岁月、青年时期……
麦家:我其实真是没有青春,我的青春全部交给了失败的《解密》,我1991年开始写,到1997年已经写了6年了也还没出来,还要经过5年的等待,到2002年才出版,也就是说这11年几乎就占有了我全部的青春。

△ 年轻时的麦家
我不像今天一样是职业作家,那个时候我还工作,都是很具体的工作:在部队是新闻干事,要给领导写讲话稿、写新闻稿,后来到了电视台的电视剧部,是专职的电视剧编剧,也有大量工作要做。然后业余时间回到家干什么?就写、看。
凤凰网读书:所以您转业的时候,已经写了五六年了?
麦家:写了6年了。其实为什么是11年,因为它不停地被人退回来,有些人退回来会提一些修改意见,它就不停地在邮路当中,它在漂泊,我也在挣扎,因为我总是不甘于此,总是想把它救出来。
凤凰网读书:虽然《解密》经过了11年的曲折才得以发表,但是您的作品只要被发表出来,就都能够得到观众、读者喜欢,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麦家:我经常会被人问到,怎样才能让读者喜欢?我说其实不知道,但你必须去寻找自己最独到的那种东西。即使是独到的,读者不一定会喜欢,但这是被喜欢的前提。所以我觉得寻找自己的独到性,这是每一个创作者必须要过的一关。找到了这一关还没有通到最后,肯定还是需要一点运气来帮助。
比方说《解密》为什么前面过不了?同样一部作品为什么2002年一出来,突然被那么多影视拍追捧?其实《解密》出来只经过一年的发酵,2003年就入围了第六届茅奖,在20部进5部的时候才被淘汰,由此可见已经走到离茅奖最近的地方了。也就是这部作品是一下子被认可的,但在之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不被人认可,就是(因为)时代的变化。

△《解密》首版,2002年10月出版
凤凰网读书:您刚刚说的是客观因素,我的感受但凡您的作品只要能够走到发表这一步,接下来与读者的连接都是非常顺畅的,您觉得这与您当时已经在电视台做编剧有没有关系?
麦家:没有关系。我一直在研究读者,但是研究读者其实说白了就是在研究。当大家都抛弃故事,甚至小瞧故事的时候,我坚信故事的魅力。我从来不相信有故事就没有文学这个说法。
我们的文学有一阵子迷茫的时候,想抛弃故事,觉得没有故事的东西才有文学性。我就觉得很奇怪,当你抛弃了故事,也就等于抛弃了人物,当你抛弃了人物,谈何文学?文学是关乎人心灵的一件事情,你把人物枪毙掉了,哪里还有心跳声?
探索性的作品是可以的,但在文学整个大家族里面,从我们最初的唐传奇到托尔斯泰,到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强大的故事是我们走近读者的一个捷径,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必由之路。没有什么其他的路,你必须要讲好故事,而且要相信故事不是那么好讲的。
故事的前提是人物,你要讲好故事,必须要塑造好人物,很多故事都会被读者忘掉,但是人物还会被记住。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们会褒奖我、认为我的东西确实广为人喜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塑造好了人物,不管是《解密》也好,还是《人生海海》《风声》也好,我里面总是有那么一两个鲜明的人物,这个人物一定意义上是带着我的标签的。

△《风声》剧照
凤凰网读书:其实您在《解密》之后,尤其2005年《暗算》电视剧出来后,大家就说麦家已经开创了中国谍战剧的先河,然后到2009年《风声》上映以后评价特别高,大家就都知道“中国谍战之父”是麦家了。当获得这种巨大的市场认可、影响力认可的时候,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麦家: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谍战之父”这个头衔。
虽然当代谍战影视确实是从《暗算》开始的,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称为它的父亲。因为我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谍战,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其实对这种盛名我是不享受的,甚至害怕。一方面我希望被承认,但当有一天它确实给我带来巨大名利的时候,我其实是深深地惶恐,一定意义上我也被当时那种名和利伤害了。
包括我后来快速地写《风语》,当时规划的是100万字,包括《刀尖》的上和下,体量都很大,写得很快,我觉得一方面是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定,另一方面后面有堆人在推着你,疯狂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变形,因为很多人对你有所期待。
甚至有些人本身会有很夸张的行为,比方说有一天一个人拎着个面粉袋,里面装着300万现金到我家里来,就丢在我餐桌前面。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们有个剧已经拍完了,马上进入后期剪辑,我们希望你挂第一编剧,不要我写,也不要什么,就是希望署一个我的名字,宣传上说起来这就是我的剧。
虽然我不能说清心寡欲,但我在名利面前其实一直比较谨慎,在这种狂轰滥炸之下,人难免会变形,有时候就写了自己不想写的东西,或者写了自己没有那么精心去写东西,下笔就难免会漫不经心,这就是动作变形了。
所以我在2011年之后有3年没有写东西,我都已经做好不写东西的准备了,我真是觉得应该把我的名和利拿出来分享给我的读者,我已经盛不下了,我的承受力很差,对名利的接受力也比较差——2011年我建“麦家理想谷”,2014年我又做“麦家陪你读书”这个公号,这三年我全心全意做这些所谓公益的事情,其实是想不写作之后找一件事做,同时也是给我内心寻求一种平衡,拿出全心全意跟大家分享我的蛋糕。
后来慢慢我觉得内心新的平衡又建立了,由于各种原因就开始写《人生海海》,写作还是我的一个宿命,逃不掉的,即使想逃最后还是要回来。

△ 位于杭州西溪湿地的麦家理想谷
凤凰网读书:我也是看到您之前的描述,您可能后来也在反思说觉得对《刀尖》有些不满意。但我们常人很难想象,那个时间点怎么就突然对自己说得停下来,有没有因为什么具体的事情?
麦家:这个确实有些宿命。首先《刀尖》出来以后,包括《风语》出来以后,虽然骂声不是那么强烈,但我确实听不到夸奖的声音,哪怕好朋友当面奉承几句说“写得不错、写得不错”,但是一听就听得出来,那个褒奖是没有温度的、没有细节的,就是一句假话,就是一个恭维。以前像《解密》即使经历了17次退稿,但有一天出来后还是好评如潮,这个我自己能感应到。
当你感应到了这个以后内心肯定是寂寞的,然后也会反思,但是在反思面前是不是能够回头?这就像一场苦恋或者说有些婚姻、恋爱进入了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当断不断时还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外力,才能去断掉它。
写《刀尖》的时候,在《风声》《暗算》《解密》的这种有影视改编的作品加持之下,确实特别热,影视圈也在追捧,文学圈也在肯定,人就会头脑发热。《刀尖》我写完以后,可以说一个字都没改,马上就发给了当时《收获》,他们也马上安排,以前一个稿子被退11年,那个稿子大概不到5天就给我回应了,说发在哪一期上。
他们先发出来了第一部“阳面”,我继续写阴面,然后要求我10月1日之前交稿,但是9月30号,我父亲去世了。最后大概还有三四千字,如果说没有父亲去世这件事,我肯定可以按时完成,哪怕拖个一两天肯定没问题,但是父亲去世,一下子就很尴尬,我就跟编辑打电话,痛哭流涕着跟他打电话,说我不能交稿了。编辑说不行啊,发了上部不发下部不行的,要开天窗的,他说给你三天时间行不行……
最后我在父亲的灵堂上,半夜三更轮到我守灵时,那些亲戚都睡觉了,唯一安静的时候,我就在父亲灵堂上写,写得最后就吐,就扇自己耳光……写作到了这个程度我觉得是很滑稽的,它成了一种笑柄,它曾经是我的生命的动力,但是今天成了我活着的一个笑柄。
一边给父亲送终,另外一边我还得给稿子送终,我觉得这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这个事件深深地教训了我。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暗示,我被嘲弄了,我被写作嘲弄了,既然它嘲弄了我,嘛要写作呢?所以我在父亲的灵堂上把《刀尖》最后的3000字写完,交给他们以后,真是痛哭了一场。
这种痛哭是一种就此别过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再也不想写任何东西了,我以后就做个流浪汉也可以,哪怕身无分文我也不怕,但是我不想受这种嘲弄。那种对我彻头彻尾的嘲弄,我觉得是深深伤害了我。所以我后来三年只字未写,我觉得这提供了一个外力,让我结束了所谓的谍战文学。
我从父亲的灵堂出来以后,我就发一条微博,说我从此不写了,至少不写谍战了。这一点我确实至今还在坚守。
我后来写《人生海海》,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一方面我已经宣布我再也不想写谍战文学,同时再写什么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做好了任何东西都不写的准备,熟悉的不写,陌生的在哪我也不知道,我也做好准备不写了,碌碌无为度过一生,后来有幸能找到《人生海海》。
凤凰网读书:听您这样讲述,您的生命里真的有很多这种宿命感强烈的时刻。
麦家:是的,所以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越来越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是一种宿命也好、命运也好在带着我走,不是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回头看,不管是年少时受的苦难也好,包括以曾经高考语文考得最差的一个人能当作家,从开始遭遇17次退稿,到今天能够源源不断写作,甚至名利双收,我觉得这一切都仿佛是在梦中。如果说是努力得来的,我确实付出了,但是我的付出难道就应该得到这些吗?这里面没有必然。
我觉得是可能是某一种力量的加持,是它在引领着我,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想做一些有益于别人的事情,包括我现在做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都是对方,绝对不想自己。这不是说我崇高,而是我恐惧,我觉得已经得到那么多了,凭什么还想不停地得到,现在做任何事情,必须在别人得到、别人舒服的情况下,自己有所得到,我才会心安理得。
凤凰网读书:刚刚聊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收获》的那篇稿子不交能怎么样?像《收获》这么大的刊物,其实也不会开天窗的。就是您一直以来的性格特点,让您不会说交不了,烂摊子甩给别人了……您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
麦家:当然他们会用其他稿子补上。确实是也是这样的,一旦冲突发生的时候,我总是退让,我说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这个就是我的一种人生准则。可能很多人说我现在做人境界真高,其实不是境界,一定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内心脆弱,你斗不起,或者说心理素质差,你不能跟人去斗。

△ 麦家 / 尹夕远 摄
我可以跟你泄露一个秘密,我最近三年一直在记录一个灵感或者一个主题的笔记,关于“一个人只能做好人”。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会冒出各种各样的细节,这很可能就是我写完故乡之后的另一部作品。
其实我想这不仅仅是我的一个人的声音,我也希望这成为一个社会的声音,就是不要鼓励人去恶,善本身有时候也是一种斗争的策略。所谓以德报怨,这也是我最近几年特别迷恋的一种人生状态,就是争取做好人,只能做好人。
Part 4 和解
“人生海海,你得意啥”
凤凰网读书:我觉得您非常喜欢写天才的故事,比如《暗算》中的阿炳,前段时间《奥本海默》上映的时候,我看到诺兰接受采访说,他也很喜欢天才的故事。
麦家:他一直在讲述天才的故事,从《致命魔术》开始,包括《记忆碎片》中,也是个天才。
凤凰网读书:对,他说他尤其喜欢去展现天才被自己的才华所困这件事情,我想知道您喜欢写天才的故事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情结?
麦家:大同小异吧。首先我觉得文艺家族其实特别青睐天才或者说奇人,我们最早来源于唐传奇,中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左传》也是堆奇人奇事。
当然文学进入了20世纪以后,其实是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当道,他们要讲究底层、讲究关怀、讲究普通人的情感,这个肯定没错,但是有一点,不管是文学还是影视,最终是要读者、观众来买单的,你要让他们来买单,就必须要讲好一个生动的故事。
其实现实生活很庸常的,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种故事是很难讲的,哪怕像我这样脾气有点怪、经历有点复杂的人,也就不过尔尔。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打造出来一种相对生动的、有趣的,不要说惊心动魄吧,至少要是有惊无险的、有一定魅惑力的这些人物故事。
一定意义上来说,天才是最有魅力的人,至于天才最后是成于斯败于斯,这也是个哲学命题——天才容易成功,天才也容易毁灭,就是当你从你所在的群体中出类拔萃的时候,你一方面是进入了聚光灯之下,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暴风雨之下,所以天才最后被自己的荣誉或天赋所毁灭,一定义上也是天才的命运。
所以不管电影还是文学作品里,经常有悲剧,甚至越悲剧的东西越深入人心。一方面生活就是如此,另外一方面也是一定的艺术规律,总是喜欢把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揉碎了端给别人看,因为这样才有所谓的艺术感染力。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生活本来如此。
很多读者建议我能不能写一本主人公有光明结局的,我一直在尝试,包括我的新作,我鼓励自己写一个最后有非常幸福、快乐、光明的结尾的主人公,但还是写不出来,这可能是由我的记忆的基因决定的,每一个人的人生或情感,都是有个底色的,我的底色应该是灰色的、悲观的,这也是由我的童年或者由我的成长之路决定了的,可能不可改变。
凤凰网读书:您会刻意地尝试写一个大团圆结局的?
麦家:我确实特别希望,尤其现在这部新作,我特别希望结局是光明的,但还是没做到,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以前写作,比方写到阿炳触电死的时候,我确实鼻子发酸,但是没有失声痛哭,但这次写作我还真写到失声痛哭,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了,控制力越来越差了,就相当于人的肌肉,肌肉特别有力的时候,你会收放自如,你能控制得了,当你肌肉消失,同样举一个重量,你会颤抖,你会失控。
我这次充分尝到了失控的滋味,有一天我突然就失声痛哭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长期住在一个寺庙的酒店,我的隔壁是临时来的,他也不认识我,那个人听到我晚上在哭,他住了一夜走的时候跟前台说,好奇昨天晚上在哭是个什么人。后来前台跟我说,昨天晚上你隔壁邻居听到你在哭,我说我自己真的不知道,后来我想肯定是写特别悲催的情节让我失声痛哭了。随着年龄的增大,内心的控制力已经失去了。
我想说的就是,我很想写一个光明的尾巴,但是最后写了一个可能是更苦的一个作品,一个更大的苦瓜出来了。
凤凰网读书:它的走向其实已经不受您控制了。
麦家:写作就是这样,如果你完全被技术的控制,它就是真正的类型文学了。我没有文学的高低优劣之分,比方说像东野圭吾现在都写了80多本书了,我觉得他更多是一种类型写作,他可以不停地自我。
首先我不承认我是类型写作,我是反类型写作,我特别害怕自己进入一个写作的舒适区,比方说我从《解密》《暗算》《刀尖》《风语》突然转身写《人生海海》,就是想逃出那种类型。
因为写《解密》《暗算》《风声》,我还是澎湃、充满好奇,也充满那种挑战未知的热情和勇气,但到了后面像《风语》《刀尖》,我觉得我已经进入了一种滑行的写作,从结果上来说,当然是令人不满的,我不能说它们是失败的作品,但是缺乏挑战的作品。

△麦家的“谍战三部曲”
我觉得进入了一种写作的舒适区,这是一个真正对自己有责任的作家比较害怕的一种状态。我后来写《人生海海》,给自己做了各种各样的规定,比方说写得特别顺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从头去看我今天写得到底怎么样,就是我害怕写得顺,害怕这个东西可能写滑掉了。
我的写作不像莫言、苏童,他们速度会很快,早年是那种一气呵成的状态,比如《我的帝王生涯》,一看就是那种天才型的作品。但我的写作从来没有一气呵成,我都是老牛拉破车,慢慢地一步一个脚印,甚至是进一步退半步,所以有一天如果说我可以一步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恐惧,我会先停下来。
凤凰网读书:我后来看您说,您回头看的《风语》和《刀尖》的时候,发现它们没有那么好的“质地”,您用的是这个词。
麦家:是的,应该是2016年吧,我去做撒贝宁的《开讲啦》,当时我的演讲词写完以后,他们的编导看了以后说,你这种对自我批判合适吗?他说我们收视率很高,你不怕被人抓住把柄,读者以后就不买你的书了。
我还真思考了一下,但最后还是很坚定,说我还是这么说,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其实我想把自己逼到墙角或者逼到悬崖,我必须告别所谓的谍战系列,另辟蹊径,重新出发。如果没有一些退无可退的那种余地,人的身上都有一种惰性,或者有一种狡猾。第一,我在微博上公布,说我以后不写谍战了;还有我在这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节目上,坦诚自己要告别这个系列的写作,都是给自己一种外力,希望自己去寻找一个新的一个出发点,所以后来就才有了《人生海海》。
今天好像觉得这个转型是成功的,但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或者在这本书被读者认可之前,怎么知道它是否成功?我在那个舒适区里其实身价是最高的,我的一部作品出来,不管是《刀尖》也好,还是《风语》好——《刀尖》电视剧已经拍过两轮,电影也拍了,《风语》也是这样,当时央视以每集85万把它收购了,还有报道说创了央视收购剧集的最高纪录——从这些层面上都没问题。
但是我知道我写作进入了危险区,进入了一种特别轻松的甚至自我的状态,这种写作是没有意义的写作。每次写作其实都是突破自己,让自己有个新的高点,当你没有高点而是从高点上往下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危险的,就当时来说我是不能认可的,可能再过5年我也认可了,我那时总觉得还年轻,那是2011年,我还没到50岁,我觉得那不应该是我的顶点,我应该去寻找或者创造新的顶点。
凤凰网读书:您写之前说想写一个不畅销的,来彰显它的文学性,就比如说《人生海海》,结果它那么畅销。
麦家:这个确实我没想到。《解密》《暗算》《风声》这些会畅销有一定道理,首先它们是天才的故事,天才总是有魅力的,人生有惊险的、精彩的故事,这都是读者喜欢或者畅销的一定要素。但是当我写《人生海海》,我要回到我的童年时代,那个时代其实本身是一个很荒诞的时代,既没有风花雪月,也没有,只有一些上的扭曲的、病态的生活状态,加上又是童年时代、农村题材,这都不是畅销的(元素),我也没想到这部这么火……
所以我经常也会想——包括《解密》当初是被退了17次稿,历经11年的等待,才开出一朵花,这朵花一旦开出来以后,它是真是经久不衰,甚至最后飞越大西洋到世界各地——有时候畅销还真不是作家或出版人或影视公司策划营销出来的,你只能准备畅销,但不能指望畅销,前提是你要写好,做好畅销的准备,但是准备好了不一定能够结出果来,有时候是运气。
当然《人生海海》我写得非常努力,很用功。这从写作技巧上来说,可能也是我最成熟的阶段,同时也是我最努力写的一本书,是因为它确实是掏心掏肺、触及到我生命最隐秘的一个角落。
但是我确实没有做好畅销的准备,我觉得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的,或者是写给我和我那一代人的。因为我们60年代这一代人,尤其是在农村,过着相对比较简单、粗糙的、没有爱的(生活),只有一种病态,吃不饱、穿不暖、缺乏关怀。那个年代在今天是其实很难被理解,这本书被接受了,我从来没觉得是因为它写得好,而是因为它命好,就像一个人,命运好比什么好都重要。
凤凰网读书:您后来有没有想到,它可能跟某一种时代情绪契合了?
麦家:有的。现代人总体来说活得相对比较纠结、比较焦虑,和《人生海海》里的主角相比,和这种大起大落、浮浮沉沉的人生相比,我们受得那点委屈或工作上一些焦虑或者挫折,真得不叫事,我觉得这样一定意义上来说上下也在安慰我们,所以也有很多文章写“当你觉得生活过不下去,去看看《人生海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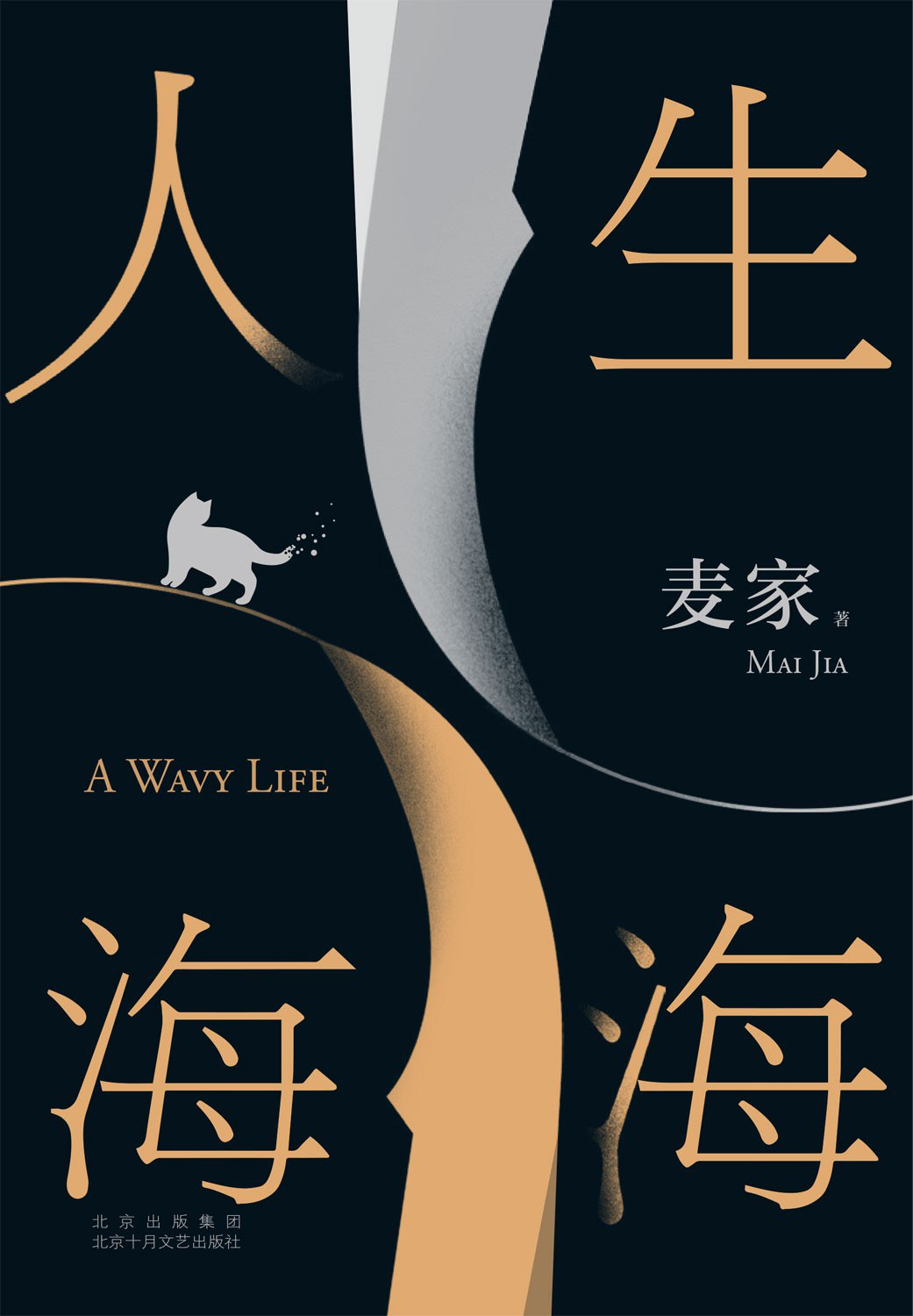
△《人生海海》,作者:麦家 /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出品方: 十月文化/出版年:2019-4
“人生海海”这标题我也觉得取得好,所以现在成为一种口号一样,很多年轻人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喊一声“人生海海”。之前我取了23个标题,出版社全都不同意,有一天我很无聊,就去看《奇葩说》,《奇葩说》里有一个小伙子在辩论中指着对方喊了一声,“人生海海,你得意啥!”我就觉得,哦,这个词年轻人已经开始用了。其实这个词早在我心里,但我不敢用,后来看他们已经在用了,我想我就跟着用吧,就是像接力棒一样把它接过来,也有幸交到了更多的读者手上,让这个词变成一个热词。
凤凰网读书:对,它好像成为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种心理状态。
麦家:因为现代人内心很需要安慰、很需要和解,而这本书、包括书名,都是提供了这种机遇,它有一定的安慰性、疗愈性。
凤凰网读书:您觉得这本书包括读者的喜欢、包括它的销量,从您自己来看,它实现您曾经说要写一本不畅销的书来实现它的文学性的目标了吗?
麦家:我从来不怀疑我的作品的文学性,不管是早期的《解密》,还是《暗算》《风声》,这些作品虽然从题材上来说不是一种纯文学的题材,但我觉得我让纯文学的疆域得到了拓展。国内以前总觉得好像写苦难,写土地,写农民,写相对比较落后、愚昧的生活才是一种纯文学,这显然是对纯文学的一种禁锢。
为什么一定意义上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是有一定的开拓性?因为我把这种题材、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新颖的人物,引入纯文学的疆域。也有人说我是当代中国类型文学的鼻祖,“穿越”“盗墓”当然是在我之后,但我觉得我写的和它们完全不一样,我的写法是传统文学的写法,只不过是让所谓严肃的纯文学里引入了一个新的场域。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时代在变,包括很多做文学研究的人,他们对纯文学的态度也在进行转变,我觉得包括给我茅盾文学奖,包括后来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被很多专家肯定,确定了我在文学圈的地位,也是一种对文学的新的开拓。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受国外现代化文学的影响,作家的害怕写故事,觉得写故事就是没有文学性,就喜欢把写成读者看不懂的、云里雾里的,(认为)这就是一种文学,甚至越自我、越私人化写作,我觉得这种文学里只有自我,没有他人,只有自我内心的一种心跳声,没有一个时代的心跳声,那肯定要走入死胡同。所以这样的写着写着被大众抛弃。
恰恰在这时候,读者厌倦了那些文学,然后给了我机会,我的写得好看,有故事、有人物,就容易传播,然后搭上时代的顺风车。这应该算我命好,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文学需要一次突围。

△ 麦家 / 摄影 柴利增
Part 5 童年
“自卑者无敌”
凤凰网读书:您给我的一种感受就好像是,一直觉得自己得到挺多的了,有一点点诚惶诚恐……
麦家:是的,这就是我的一种本性,也是我的一种理性,我的内心一直很自卑,今天我也没有摆脱。我曾经很为自己的自卑心理惭愧或心怀不满,但慢慢我又接受了,甚至开始欣赏我自己的这种不自信,我甚至觉得一个人过于自信,其实不见得是好事。
人都说“仁者无敌”,其实是“自卑者无敌”,你总是担心没做好,所以会不停地努力,不停地反复修改,总担心别人不满意,这肯定一种自卑心理。
包括我平常面对生人都会紧张,人家说你到了这个份上应该阅人无数,自信心应该都培养出来了,但我天生是那种性格,可能也跟自己相对比较艰辛的童年有关,一是在乡下,另外在那个时代,我们这种家庭地位特别低。
凤凰网读书: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作为外人都会想,麦家老师以前可能会自卑,到现在已经这么厉害了,怎么还会自卑呢?
麦家:现在真的很自卑,有时候是控无可控,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这种心绪。我只要一站起来说话,台下有观众,背上就有出汗,观众越多,我背上出得汗越多,而且根本无法控制,坐下来会好一点,这好像是一种身体记忆一样。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看着我的父亲在台上被批斗,所以我每次站到台上,就会下意识想起童年那种最煎熬的记忆,看到父亲在台上被批斗的记忆就会马上会被唤醒。当这种记忆被唤醒的时候,你自然就变得很矮小、很卑微,这是理性控制不了,我觉得它已经进入了我的潜意识。
凤凰网读书:就是虽然您站在那里,知道底下都是掌声、鲜花……但您的肌肉记忆马上就会回来。
麦家:对,我就是没法控制。我感觉到人有时候挺有趣的,同时也挺无奈的,就是你控制不了自己,你不知道如何能够摆脱童年或内心的阴影。哪怕我今天读了那么多书,见了那么多高人,但是依然没有人能教我怎么样忘掉自己过去比较不堪的那种记忆。
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改造自己,让自己摆脱年幼那些不美好的记忆或情感,但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后发现确实完成不了,现在反而心态比较平和,与其抗争不如与其和解,我拥有它算了,就像身上一个胎记,与其摆不脱,干脆我认它为宿命,认它是生命的一部分。现在相对来说比以前那个感受要好多了,所以外面也能看到一些我所谓的形象。

△年轻时的麦家
凤凰网读书:我觉得您从小到大其实没怎么变过,比如说您会希望书架擦得一尘不染,您会希望“麦家理想谷”很有秩序,您自己内心的秩序也是非常强的,对吧?
麦家:说一个小细节,比方说回家或出门,我的鞋子肯定放得非常整齐,我甚至威胁我的家人说“鞋子不放好,出门可能就会受委屈”,我对秩序有一种神经质的强求,这肯定活得挺苦。
凤凰网读书:您觉得这与您上学的时候学的专业有关系吗?
麦家:没有关系,就是跟童年经历有关系。
因为我曾在最底层,最底层一定意义上来说,就不能出错。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你的父亲是个或富豪,你的童年会活得很轻松,不怕犯错,你如果犯了错,有人给你兜着,你会活得特别无忧无虑,这样的人可能会非常阳光,也可能会变得很放肆,但这些人肯定是自信的。
我的童年给我养成了一种我不能犯错(的习惯),我的任何一个错误都会被加倍惩罚,以至于曾有一个极端的,我经常跟人举例子——小学二年级上课的时候,那是个下雪天,我坐在窗边,有点雪花飘到我脖子里,其实南方下雪天很冷,我就趁着老师写黑板的时候站起来去关窗户,我想让关窗户不发出声音,但人在岁的时候控制力很差,就发出声音了。
老师就回头,问我为什么关窗户,我说雪花飘到我脖子里了。他说你冷吗?我说是。他就说,你头上戴了那么多三顶“黑帽子”,你还冷。这就是那个时代。
凤凰网读书:怎么能这样对一个小孩呢?
麦家:这就是那个时代。我就在那个时代里、在那种环境下、在那种特殊的家庭里长大,从小我形成了一种惯性——你不能出错,你必须要小心谨慎,当有冲突的时候你要及时回避。
以前一直为此苦恼,觉得好像身上缺乏一种斗争精神,缺乏一种阳刚之美,但慢慢我现在接受了这个缺点,甚至也安慰自己觉得这可能是我的优点,就是身上一点攻击性都没有,一直在寻求一种自己安身立命的舒适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内心修炼的方式,我觉得可能也是每个人最后要摆渡自己的一种方式——你不能指望别人来摆渡你,只能指望自己来摆渡自己。
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付出或者以前的苦难,现在变成了我身上一种独到的力量,就是总能够及时把我遇到的一些危险或者一些难关度过去的一种力量:一是让我很小心,另一个是能够及时退让。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德,至少是像我这样的人需要的一种美德。
凤凰网读书:这个经历会让我觉得,下一次再有雪花飘进来,您是不敢关窗户的。
麦家:那肯定不敢。我也曾跟人讲过,学校开运动会嘛,50米跑我第一名,没有奖状,100米跑我第一名,也没奖状……奖状都不给你。
直到1981年我参加高考,考上军校。1981年按说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了,已经拨乱反正了,但农村永远比城里慢半拍,还是活在一种特殊时期的氛围当中。但是军校不看成分了,就是根据成绩录取,我们村里还有人去告状,觉得我们这种家庭不应该去从军,从军是应该是一片红的家庭才可以。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讲得这些像天方夜谭一样不可理解,但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过去、我的童年、我的少年。
凤凰网读书: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才会让您后来比如说写一篇稿子,就是能够一直不停地改,它让您有了一种很笨拙的东西。
麦家:是,对我来说,受打击或者说有挫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我已经很习惯这样一种被打击、被打压的状态了。所以我能够遭受17次退稿,依然坚持不放弃。
但我也感谢那11年里的17次退稿,因为反复退稿、我反复修改,其实像打一块铁一样,我被反复地打,就真的打得很坚硬了,我相信我的写作技术和艺术这些关卡,我是过得很好的。
中国有很多作家年少成名,但很快就江郎才尽,我觉得他的基本功就没打扎实,就是他成名太快了,就像一朵花,花开太早不是好事,花开太早就会谢得很快;就像一棵树,长得很快质地就是松的,就难以去当一个大梁……慢慢长大、慢慢被磨砺的东西,它会更坚硬,也更锋利。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感谢17次退稿,它像是把我压在一颗大石下面,让我一直在压抑中,但是有一天我钻出来了,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我的生命力肯定是强的,一般情况可能不会把我打倒了,所以我至今还是有蓬勃的创作力,每天都有写作的冲动。当然我也在有意识地控制写作的数量,因为我不是一个高产作家,我也不想当一个高产作家,我一直在慢慢地写,几年写一部,争取每一部都被读者喜欢。

△ 麦家
凤凰网读书:您提到您刚刚写完自己的一部新作,听起来不是谍战剧?
麦家:不是,应该说还是故乡题材,因为我也想写一个所谓的“故乡三部曲”。写作跟挖井一样的,当你看到这里有油,你不只挖一口,肯定要挖充分,可能这里要开一个井,那里还要开一个井。我还是有写“三部曲”甚至“四部曲”的想法,现在第三部曲其实也写得差不多了。
凤凰网读书:第二部里面的人物跟第一部《人生海海》里,有重合的吗?
麦家:没有。应该也是像《解密》《暗算》《风声》一样,虽然都是一些天赋异禀的情报人士,但他们故事没有关系的,只是从题材上,年代上,包括精神取价值的取向上,是一个体系的。
我今天第二部,包括准备当中的第三部,和《人生海海》也是一样,故事、人物没有关系,只是精神层面、时代层面、价值取向可能成同一个体系。
凤凰网读书:大概也还是您童年那个年代?
麦家:对,因为你一旦扒开了那个世界以后,往往一本书是表达不了那些情感的。
凤凰网读书:所以现阶段写作计划或者小目标,是把三部曲或者四部曲写完?
麦家:对。我也不知道写什么了,也许可能就不写了,随时做好不写的准备。如果生活中能够找到让我开心、让我打发时间的方式,以后我就不写了。
其实写作挺苦的,当然苦中有乐,我至今仍然觉得,对我来说,写作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之一,也是我活着的一种方式。
我有时候怀疑写作的人的价值,因为好作家、好作品太多了,今天你写得挺开心,但你不知道它最后能不能留下来,当你这么问的时候,你会怀疑自己写作的意义。当然今天我觉得写作蛮有意义,它确实安放了我的时间,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安放自己,是写作让我把自己放下来、心安下来。
但是如果我能够找到一种不写作依然活得开开心心的方式,如果有一天没有写作我依然可以安心地活着、充实地活着,我会毫不犹豫放弃写作。
Part 6 关卡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自己”
凤凰网读书:刚刚您提到《神曲》,说这个世界上如果留300本书,就一定有它一本,您刚刚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究竟有没有意义,是在跟这些非常伟大的作品暗暗比较吗?
麦家:不敢比较,这不是谦虚。首先我们这种写作进入历史不是你说了算,谁说了算我也不知道,是历史说了算。当然我写作也不是为了进入历史,我想说的是好作品太多了,今天我们说300本,其实与300本比肩,同样好的可能至少有3万本,但它们没有成为我说的300本,这里面有很多机缘巧合。
我只能说我争取进入3万本,至于怎么能从3万本里面跳出变成300本,我觉得这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到的。我对每一个文字都负责,我愿意用三年时间去构思一部《人生海海》,同时我也拿出五年的时间来写,每一个文字都被我亲吻过抚摸过不止一遍,也不止100遍,那是肯定我是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进入这3万本。但能不能进入3万本我也不知道,更不知道从3万本能不能进入300本,这就是生活的无意义。
但是一定意义上来说,正因为生活是无意义的,我才要不停地写作,因为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你才要去追求有意义,就像是人本身肯定是要死的,所以你想活好每一天,这好像是个悖论,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凤凰网读书:而且写作对您自己有意义,对您的读者也有意义。
麦家:是,我一直就这么安慰自己,包括我今天建“麦家理想谷”,包括做“麦家陪你读书”这个公号,我总觉得这对人是有意义的,不一定他们都会喜欢我的书,但我想他们只要爱上书,对我来说都是一件积功德的事情。
凤凰网读书:我以为“麦家理想谷”是您开了个书店,昨天来了以后发现这里的书很破、很旧,原来这里是一座小图书馆。
麦家:这里的读者确实来自全国各地。我们在网上也有“陪你读书”,现在已经第328本了,这些书可能会成为读者重点过来读的,所以绝对是被翻烂的,可以说没一本完整的书,但是每一本破烂的书其实都在缝补读者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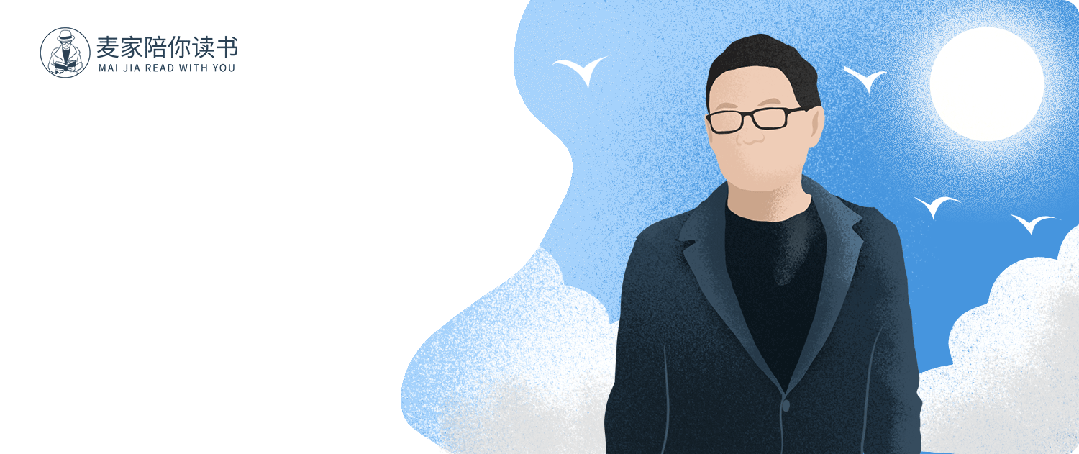
△ 图源“麦家陪你读书”公众号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陪大家读1000本书。人生不需要1000本书,1000本里有100本能够滋润你就可以了。
凤凰网读书:您打算多长时间带着大家读完这1000本书?
麦家:20年,每年50本,从开始以后一直没间断。我觉得坚持最大的鼓励或者最大的动力来自于读者,有人愿意接受我的陪读我就有动力。一定意义上来说,也看到了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意义在了,动力就有了。
最怕的就是辛辛苦苦做了,做出来的东西别人不爱看。如果这里没人来读书,我的公号没有人来听书或者看书,那是对我莫大的嘲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的悲哀。
做“麦家理想谷”包括“麦家陪你读书”,坚持下来其实挺难的,我经常有退缩的时候。
凤凰网读书:什么时候会退缩?
麦家:比方说人员流动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志向变了,刚开始他跟我一样愿意陪人读书,但慢慢他觉得这个时代读书人的力量越来越微弱,他可能也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他离开这个团队,我就要重新去培养人,这也是很难的一事情。
有时候就是咬着牙在做,当然咬着牙我也会寻求自我安慰,我觉得陪人读书,就是劝人向善、向美,这是一件积功德的事情,我不求自己在这里面得到回报。有时候挺过去了,本身也是一种成长,就一关一关过呗。

△ 2017年,麦家理想谷主办“一个人的私奔”文化夜聊现场
凤凰网读书: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网友归纳说您人生中过了三关,第一关是写作关,你通过写11年、被退稿17次,终于出来;第二关是名利关,您获得最大的财富、名声以后你想要叫停它,重新开始去写《人生海海》;第三关是和解关,您跟命运和解、跟童年和解…… 当然这种划分非常简单粗暴,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感觉?
麦家:他归纳得还是有他的道理,确实我人生大的逻辑或者轨迹就是这样。不仅仅是我,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关,没有一帆风顺的人。虽然我有一定的特殊性,可能是时代的原因,毕竟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经历也比复杂。
能不能过关,我觉得一是要靠自己,有时候要靠天意,你努力去克服,至于最后能不能过关,真的要顺应天意,有些关就是过不了,你就熬着过,熬着过也是一种过。今天好像说起来我被退稿17次、坚守11年,好像很轻松,但那11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熬。也有可能熬不出头,熬不出头我可能就有另外一种人生,另外一种人生也不见得比今天差,可能也许我会成为马云。
到了今天,如果跟别人分享人生经验,我想分享的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自己,放弃自己才是真正的懦弱。你不跟人争、不跟人斗不是懦弱,你把自己完全放弃了,面对挑战或者面对挫折的时候,你不给自己加一把油,我觉得那是懦弱,这样的人生可能到了最后会后悔。
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怎样在没有意义的人生当中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可能就是要在面对这些关卡的时候能够去挑战。你至少有一个挑战的行为,至于结果如何可以交给别人或者交给老天,有时候确实我们很难把控结果,但是我相信不管怎么样,所有的门槛都可以迈过去,迟早而已。
凤凰网读书:就还是那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
麦家:对,过不了也没关系,但是最可怕的是,你人生没有一个关要过,我觉得这种像白开水一样的人生,首先我怀疑它是存在的,其次如果你真中了彩票,一生不需要过关,一定意义上说我不会羡慕他,我甚至只会同情他,因为他的人生太华丽,华丽得苍白了。
今天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富得只剩下钱了,这也是一种悲哀。如果他家里有金山银山,但是他却是个空心的,不会看电影、不会看,甚至连一个基本故事都不会讲述,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再有钱也是苍白的。
凤凰网读书:当时读您的《博尔赫斯和我》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您说“甚至没感到生活在爱情或金钱中是光荣幸福的。但沉醉在博氏书籍中,确实感到了光荣和幸福”……
麦家:我觉得我在世俗面前没有太大的需求,但是文学一定程度上成为我的宗教,它成了我形而上的一种追求。当我的世俗生活即使非常寡淡,非常无趣,甚至苦难的时候,依然有文学在陪伴我,我觉得我的人生依然是丰满的,因为有了文学的陪伴。
其实我是活得比较抽象的,我一直说我满足于以抽象的文字来完成自我,我也曾经说过一种极端的话,说如果有一天有一种法令审判我,让我不准阅读、不准写作,我可能就撒手而去了,因为我离不开这些东西。














